
首页新闻中心常州翻译公司《李健吾译文集》出版:文学翻译的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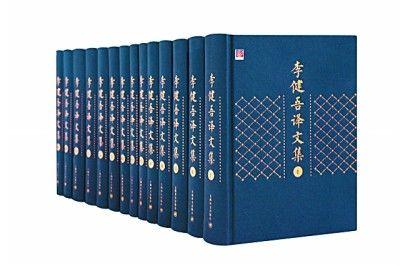
《李健吾译文集》(全十四卷)李健吾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李健吾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成为新中国法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军者,由他翻译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莫里哀的喜剧全集等,成为法国文学翻译的典范之作。《李健吾译文集》是李健吾先生的译文全集,汇集了李健吾存世的所有翻译作品,共十四卷,三百五十余万字。该文集的出版在国内翻译界、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都有填补空白和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如果生生地要将健吾老师和自己拉上关系,未免矫情。健吾老师去世的时候,我还没能接触到法语。甚至就汉语而言,也仅停留在认识不多的一些字的阶段。待到后来接触了法语,读了一些法国文学的作品——当然也先是读译文,然后才慢慢进入原文——中间总也隔了五六年的功夫。
和我这一辈乃至上一辈的法语译者一样,如果讲起未曾谋面的师承,首先提到的总是傅雷先生。学了法语,起了要在两种语言间游弋的心,最先会找来傅雷先生的本子,而且一定是《约翰克里斯多夫》首当其冲。这个选择,到现在为止也还是不错的。在某种程度上,法语文学的翻译今天能有这样兴盛、严谨而人才辈出的场面,应该也和傅先生的“家训”相关。
但是健吾老师不一样。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此。这个不一样,既是因着他字里行间透出的亲切,也是因着他的才情。有时我会胡乱地想,如果真是有幸当面聆听教诲的老师,傅雷先生一定是让我且敬且“畏”的,畏不入他的眼,畏哪里做错了,不得原谅,因而我会只是认真完成他布置的作业,不敢有一点惰怠、超越或逾矩。但健吾先生应该是能够时时上门讨教和讨论的,翻译之中还要夹带着一些创作的私活,暗地里希望能够得到健吾先生的首肯,从此便有勇气走上创作的道路。
生动传神、独树一帜的译笔译品
我这一辈人,但凡做过一些文学梦的,哪一个没有被健吾先生那些绮丽的比喻和充满想象力的词语吸引过呢。例如他写泰山的水,“碰到嶙嶙的乱石”“激起一片雪白水珠,脱线一般,撒在洄漩的水面”;又如他悲切的《切梦刀》中,他说,“我活着的勇气,一半从理想中提取,一半却从人情里得到。而理想和人情是我梦的弼辅。”有一段时间,我深陷于对“洄漩”“弼辅”这一类现在不再常用,可别有一番味道的词语里,经常在我不像样的写作里怎么也要用上两三个,不能不说是健吾先生的影响。
的确,我好像一直是到读了《包法利夫人》,才知道健吾先生也是法语翻译界的“祖师级”人物之一。是先读了健吾先生译的《包法利夫人》,才爱上了福楼拜,还是先爱上了福楼拜,才读到了健吾先生译的《包法利夫人》,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健吾先生的译文是我后来在各项研究和各类课程中引用最多的译本之一。讲文学的现代主义,讲福楼拜,讲现代社会物质对人的规定性,健吾先生译的福楼拜仍然不失为最好的例证,因为在他译笔下呈现的福楼拜偏爱堆砌的名词,是绝对能够解释为什么物可以诱发欲望的。例如爱玛进入昂代维利耶侯爵家餐厅的那一段:
爱玛一进去,就感到四周一股热气,兼有花香、肉香、口蘑味道和漂亮桌布气味的热气。烛焰映在银罩上,比原来显得长了;雕花的水晶,蒙了一层水汽,反射出微弱的光线;桌上一丛一丛花,排成一条直线;饭巾摆在宽边盘子里,叠成主教帽样式,每个折缝放着小小一块椭圆面包。龙虾的红爪伸出盘子;大水果一层又一层,压着敞口筐子的青苔;鹌鹑热气腾腾,还带着羽毛。
因为是译者,健吾老师并不夸张,但是福楼拜在视觉——例如颜色和形状——或嗅觉——例如混杂了食物和奢侈生活方式的“热气”——的用心,健吾老师却一点不漏地用中文逻辑为我们“顺”出来了,而且妙就妙在,与福楼拜在原文中的逻辑一点也不违和。
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早在翻译《包法利夫人》之前,健吾老师就已经写了《福楼拜评传》。《福楼拜评传》的初稿完成于1933,当时他还在法国游学,只有27岁!游学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深化对福楼拜的研究。用柳鸣九老师的话来说,迄今为止,这本在八十几年前就已经完成初稿的《福楼拜评传》也仍然是中国对于福楼拜最好的研究。没有之一。在《包法利夫人》的译本序中,健吾老师在谈到福楼拜对于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态度之后,转而写道:“福楼拜僻居乡野,埋头写作,和(现实主义)运动毫无往来。然而在没有作品能说明现实主义的正确内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种要求。也正是这样,圣佩夫(即圣勃夫)才把它们拉在一起”。虽然没有强调,但是健吾先生在序言最后提醒我们说,“他(福楼拜)反对作者在作品中表示意见”,却“并不因而就少泄露他对时代的看法”。可惜的是,在今天各种“外国文学史”或“法国文学史”中,很多文学史家还依然只满足于为福楼拜简单地扣上一顶“现实主义作家”的帽子,因而也导致了相当一部分读者对福楼拜所塑造的包法利夫人或者笔下的那个“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了简单理解。
恒心恒力的研究家型翻译家
如果说在中国的文学翻译历史上,集评论家与翻译家于一身的,并不止健吾老师一人;集创作家与翻译家于一身的,也并不止健吾老师一人;但是能够集评论家、作家(剧作家、小说家)与翻译家的,却少之又少;在这三个领域能够做到最好的,就更数不出几个了。或许,和健吾先生交好的郑振铎先生算是一位吧。关键在于,研究的深入并没有影响健吾老师的生动译笔,而创作的经验却也没有让他在翻译时“时时技痒难耐”,这就足够我们这一代译者学习一辈子的了。健吾老师对翻译的事情有自己的见解。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写过《中国近十年文学界的翻译》,指出译者应该“不做作,不苟且,以持久底恒心恒力将原作用另一种语言忠实而完美地传达出来。”——当健吾老师结束了翻译的一生之后,为我们留下了十四卷的译文(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李健吾译文集》),译作既包括他所专注研究的福楼拜、莫里哀,也包括司汤达或者其他一些19世纪重要法国作家的短篇,应当也是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译者的“恒心恒力”了。更是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专家型的翻译”。让我感喟的是,健吾先生译《包法利夫人》不仅有序,而且序也是与时俱进的。因为在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的第一版里就有他当作序言的《包法利夫人的时代意义》,而在1958年人民文学的修订版里,他又重新作序,到了1979年再次修订的时候,他干脆把他的序也重新修订了。更何况在序之外,健吾先生还译了《关于包法利夫人的公诉状、辩护状和判决书发表于诉讼》,可谓“全套”。读者也能据此更好地了解到1856年至1857年《包法利夫人》遭到诉讼的前后以及家族聘请的大律师塞纳精彩的辩护词。除了能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包法利夫人》和福楼拜之外,译者这些“额外的”工作恰是道出了文学翻译的真谛: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资料功夫,与作者的所谓心灵相通都是不着边际的事情。
撑起汉译法国文学的一块天地
提起莫里哀的翻译,我很喜欢韩石山先生在《李健吾传》里提到的一则轶事。早先因为上海暨南大学的聘任,健吾先生三十年代游学归来后不久就在上海安顿下来,陪着上海一起渡过了抗战的“孤岛”时期。因为出身,也因为上海期间的一些特殊事件,健吾老师在上海并不完全如意。所以,即便作为上海剧专的创始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本应该发挥他能力的位置。好在他在郑振铎先生的帮助下,回到了北京,进入后来成为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但是,就在他才离沪返京后不久,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戏剧专家来北京上海两地的戏剧学院讲学,有苏联专家提到中国“没有一个人懂得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中央戏剧学院当时的院长欧阳予倩立刻反驳说李健吾能讲莫里哀。健吾老师讲的莫里哀给上海戏剧学院编剧师资进修班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他的讲解“简直像演一出戏”,“显示了他对莫里哀巨作的精通和表演才华”。可不是吗,除了评论家,剧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外,他对莫里哀的精通,还因为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中学时候就以男扮女装的表演闻名戏剧界了。当《好笑的女才子》里的父亲高尔吉毕斯拿两个女儿没有办法道,“我用不着风度,也用不着风情”,当《讨厌鬼》里的大山劝慰老爷说,“老爷,乐中有苦,就是生活,天下不会样样事如意的。上天要世上人都有讨厌鬼,因为不然的话,人就太快活了”,这对白的节奏就已经明白地告诉读者,译者绝不是一个只知字字对译,完全不知舞台效果的硬译者,可再看着原文,就知道他也绝不是一个为了舞台效果而牺牲掉了法语(不要忘了我们将法语称作“莫里哀的语言”!)和莫里哀的译者。
今天,戏剧的翻译不再有当年的荣光,怕是也和戏剧翻译界不再有健吾老师这样的译者相关吧,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说小说的翻译并不见得要求它的译者也是一个小说家,戏剧的翻译恐怕还是要求译者有舞台的经验,有充沛的创作者的激情,有对词语的敏感,有把握文字游戏和体现游戏文字的能力。这样高的要求,健吾老师不在了,恐怕还真的难有后来者。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健吾老师的翻译就是无可挑剔的,就像任何人的写作都不是无可挑剔的一样。柳鸣九老师在《李健吾译文集》的序中说,“化派的主将几乎没有一个没受到过攻击”,健吾老师也不可避免。然而以“硬伤”或者“误译”为由诟病半个世纪之前的译者未免有些不厚道。试想,当年从北京到巴黎,健吾老师和他的老师朱自清先生走了半个月,这又如何可以和让世界几乎同步的网络时代相提并论呢?用心的译文,本着对作者的尊敬态度,本着对读者的负责态度,显然都是各有所长,用不同的方式,增加了目的语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况且文学翻译从来不是唯一的。我始终信奉本雅明的话,原文阐释的空间越大,就越会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翻译,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语言里。并不是因为先前的译者不合格的缘故。在健吾老师的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他的译文仍然不失其趣味,也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能与半个世纪之后的其他译文并立,能以一己之力撑起汉译法国文学的一块天地。
这块天地,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呈现给我们的十四卷《李健吾译文集》。韩石山先生在《李健吾传》里曾经说过,虽然他以为会到来的“李健吾热”始终没有到来,他坚信不疑的一点是,“不管再过多少年,总有喜欢李健吾的人”。我坚信不疑的是,作为晚学后辈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为此我想,我喊一声“健吾老师”,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冒昧。
推荐阅读:痴情的翻译家,世界的《红楼梦》【发布时间】2020-08-03 【信息来源】管理员 【浏览点击】1993次